以笔为剑,书写传奇
——读艾芜《南行记》
字数:1782
2024-01-03
版名: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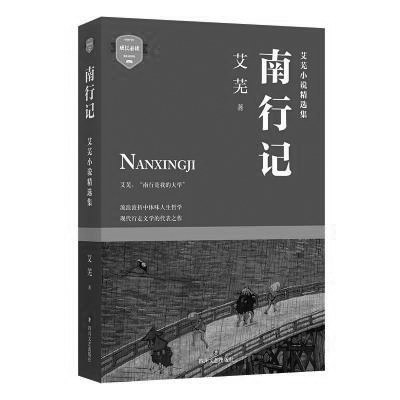
□唐明霞
《南行记》是艾芜的短篇小说集。艾芜,原名汤道耕,四川新都人,中国现代作家,与巴金、张秀熟、马识途、沙汀并称“蜀中五老”。
1925年的夏天,艾芜年方二十一,为逃避包办婚姻,同时又受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的鼓励,踏上南行的流浪之旅。他从成都出发,途经云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历时六年,最终辗转抵达上海。《南行记》就是以这段时间的流浪经历为基础,写成的短篇小说集。
书中的故事像江湖传奇。
《山峡中》讲的是一群山匪组成团伙,在市集上耍声东击西的把戏,以偷盗为生。小黑牛在集体“做活”时被打成重伤,迷糊中说出“你们害了我呀”“不想干了”的话。那是个黑咕隆咚的夜,山风呜咽,江水咆哮,在老头子的授意下,同伴们将小黑牛扔进了咆哮的江水。而对于想要离开的“我”,却是另一种结局:我早晨醒来,发现同伴们都不见了,如果不是灰堆旁边的木人儿以及留在书里的三块银元,我几乎以为这是我做的一场荒诞不羁的梦。
《松岭上》写一个挑着杂货担子,爬坡上山做小生意的老人。他寂寞,只有烟酒是他的朋友,归途中,他像孩子那样放声唱歌,他做生意时是个有趣的人。他是个奇怪的老头儿,他说要嫁一个女儿给我,他指一下手中的酒杯,又指一下床上的烟枪:“她……她……随便要哪一个都可以的。”还说:“这样我们才会亲亲热热地过日子呀。”另一个小贩却叫他“老妖怪”“老魔头”,说他原本是老爷家的长工,偷米养家的事东窗事发,他被毒打,他的妻子被老爷侮辱,他杀了自己妻子、儿女,又杀了老爷全家,然后逃到夷地。
这些故事诡谲怪诞,但读来却没有荒谬感,甚至让人觉得真实可信。或许因为小说都以第一人称叙述,拉近了作者、读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也或许是细节描写使人物显得饱满、真实。
顽固倔强、脾气暴躁的匪首老人却屈服于女儿的天真撒娇——这说明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温柔的父爱。大家把小黑牛扔进江水之后,都默无一语地悄然睡下,可见这件事的结局是谁也不高兴发生的——他们虽以偷盗为生,可人性中隐藏着的恻隐之心微露端倪。“老妖怪”在做生意时,和谐地同姑娘、孩子们开着玩笑,他一会儿伸着手掌摸摸小孩子的下巴,一会儿尖起指头抚抚女孩子的头发,活像白发的老祖父在逗孙儿孙女玩耍一样。这些生动准确的描写,凸显了人性的弧光,增强其性格的立体感和现实感
南行六年,艾芜尝尽人世艰辛,他发现了黑暗社会中底层人民的生活真相与生存逻辑,他真实书写社会黑暗、江湖险恶,书写那些在黑暗中挣扎求生的人。
《松岭上》中的老人有点像《水浒传》里快意恩仇的英雄好汉,被压迫到一定程度时,灵魂中的恶性突然爆发,变得杀人不眨眼,然后独自远离家乡。梁山好汉有水泊梁山这块世外桃源,老人却没有,伴随他一生的只有落寞、悲苦。
《山峡中》,魏老头子见惯了江湖上的血雨腥风,在他眼里,挨打根本不算什么事,他教训小黑牛说:“吃我们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哪!”“对待我们更要残酷的人,天底下还多哩……苍蝇一样的多哩!”鬼冬瓜说:“是呀,要活下去。我们这批人打断腿子倒是常有的事情……你们看,像那回在鸡街,鼻血打出了,牙齿打脱了,腰杆也差不多伸不起来,我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在笑吗?”这是一群被世界抛弃,境地悲惨的人,他们在刀尖上生活,在血地里摸爬滚打,他们以仇恨回报生活的无情,以残酷武装饱受欺凌的人生,以血腥暴力对抗吃人的社会。
《南行记》是小说,可它不吝写景抒情。艾芜将风景代入心情,将情感融入文字,不仅用精彩的对话描摹,还用场景渲染、心灵独白展示人物的情绪,因而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艾芜坦言,他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爱和恨,痛苦和悲愤”。
《在茅草地》里,“我”以为即将获得一份工作时,他写道,“一个追求希望的人,尽管敏感着那希望很渺小,然而,他心里洋溢着满有生气的欢喜……这山里的峰峦、溪涧,林里漏出的蓝色天光,叶上颤动着的金色朝阳,自然就在我的心上组织成怡悦的诗意了。”当希望再一次落空时,他愤懑,“谁叫你轻信一个陌生人的甜言,被骗到了这么一条绝路,倒霉乃是活该。”该欢喜时绝不遮掩,文字浪漫如诗;该愤怒时毫不隐忍,语言直白激烈,这是一种“真”。
那时的艾芜年轻,如闯荡江湖的少年郎,以笔为剑,书写传奇,剑招虽未炉火纯青,但少年意气风发,自信而少拘束,文字里充满虎虎生气。
后来,艾芜成了左翼作家,作品中再难见写《南行记》时的激情,但多了股历尽沧桑的朴厚,读来更显余韵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