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微笑着轻唱人生的牧歌
——重读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字数:1154
2023-09-27
版名: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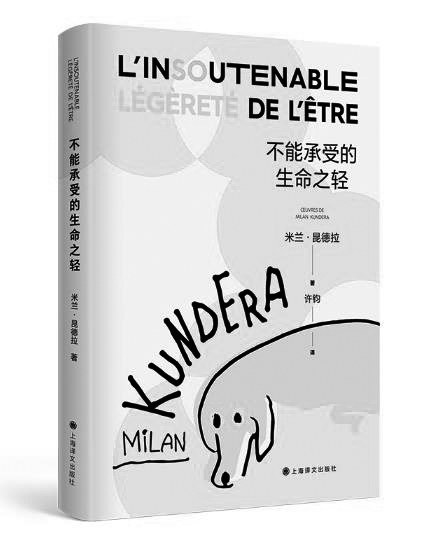
□刘 敬
“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米兰·昆德拉的哲理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从对生命的“永恒轮回”之探讨入笔,运用反讽的手法,以生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托马斯与特蕾莎、萨比娜之间的感情生活——他们彼此的纠结、缠绵、忠诚,以及背叛。同时,又不仅仅止于此,亦引领读者陷溺于对人生的轻与重、灵与肉、屈辱与媚俗等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中。
应该说,小说第一部分的前两个小节,还是比较“晦涩”的,恰似北京大学教授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一书中所言的那般,“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令人望而生畏。随着特蕾莎的出场,小说开始变得“通俗”起来,情节呈现出很强的节奏感,一如贝多芬的音乐。
特蕾莎,这个被托马斯从“涂了树脂的篮子里抱出来,安放在自己的床榻之岸的孩子”,缘于其母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露着身子在房间里行走——否定人与人肉体的差异,从而否定灵魂差异的“重”,选择了抗争,选择了对于灵与肉的绝对统一的追求,从布拉格到苏黎世,再回到布拉格,一直都无法逃匿地挣扎在痛苦的边缘——想依附,偏偏无可依附;怕背叛,偏偏难阻背叛。她避“重”求“轻”,最终,压抑的灵魂虽浮到了肉体的表面,但又蓦然省悟,那些“轻”竟是自己难以承受的,甚至噩梦连连,唯余恐惧,以致不得不将生命的全部重量维系在小狗卡列宁的身上,而卡列宁,却患了癌……
与特蕾莎截然相反,萨比娜却是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她的那顶黑色礼帽,是她强调自我感觉、拒绝服从秩序、不向媚俗低头的最有力见证。她对托马斯来而不拒,是因为他站在媚俗的对立面。她从来都渴望着全身心地投向未知的世界,挥挥手,从布拉格奔赴日内瓦;再挥挥手,又从瑞士赶往巴黎,直至到了最“轻”的美国……但,媚俗无处不在。选择了“生命之轻”的萨比娜,一次次毅然决然地背叛,最终亦无法逃脱人性媚俗的“重”。
再说托马斯,这个“在情妇们眼里,带着对特蕾莎之爱的罪恶烙印,而在特蕾莎眼中,又烙着同情人幽会放浪的罪恶之印”的家伙,尽管他是个出色的脑外科医生,眼中却揉不得责任的“沙”,内心毫无负担可言。戴上了结婚戒指后,因特蕾莎对于灵与肉统一的执著“步步紧逼”,加上不合时宜的言论引发的接踵而至的烦乱,终于迫使托马斯沦为了玻璃擦洗工,最后成了乡村公社的卡车司机,直至与特蕾莎双双殒命于雨中的车祸……
小说意象繁复,不仅有对两性关系本质上的探索,更有充盈在字里行间的隐喻式的哲学思考。米兰·昆德拉为展现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以随处埋下的伏笔与巧妙的线索,给读者带来了许多“意外”惊喜与乐趣。然而,谁又能在人生的“轻”与“重”之间自由自在地轻唱牧歌?掩卷,我仿佛看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微笑——凝重的,费解的,讥嘲的,冷到骨头里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