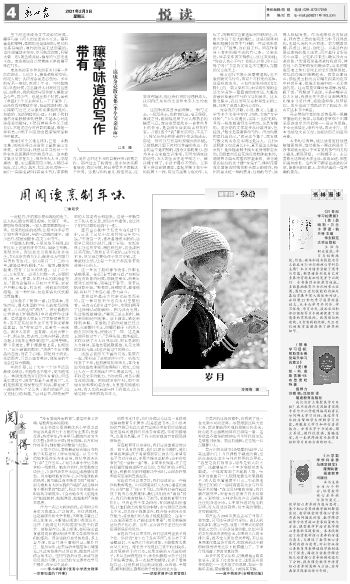本期发布:
带有穰草味道的写作

王 晓
里下河还未成为文学流派的时候,穰草与里下河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穰草就是稻草啊,柔顺的也是坚韧的,经用的也是易腐的,难闻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也许会随脚步匆匆、岁月纵深沉睡,只要火柴一划,就会被点起,穰草的气息无处不在。庞余亮说自己带着洗不净的穰草味在写作。
庞余亮的家乡和我的家乡只隔一片茫茫湖水。大地之上,藤蔓都纵横交错,何况人呢?认识庞余亮是必然的。多年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当时就慨叹:早些时候,怎么就没人对我说过这些话,如果有,我的阅读与写作盲人摸象定会少些,再少些。也是在那个时候,读到了单篇《半个父亲在疼》,一下子呆住了,还没有看到哪位作家,如此披沥肝胆、掏心掏肺写自己父母亲所有那些明亮的、灰暗的、包括阴暗的心理。打破了我们通常对舐犊情深的理解,不是冰心对纯洁母爱的歌咏,不是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不是龙应台对背影的凝望,那是一种另类,百转千回里饱含着深情厚谊和中年解读。
重读《半个父亲在疼》,已是一本散文集,刚刚获得江苏省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荣誉加身,我想从中寻找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奢侈的到底是什么。这本散文集分父亲在天上、报母亲大人书、绕泥操场一圈、永记蔷薇花四小辑,大都旧事短章,父亲、母亲、故乡、大学、读书、写诗……最后一篇篇名就叫《寂寞小书》,寥寥数行,是作者对这本书的自我评价:寂寞之作。那些过去了的惆怅、泪水和欢笑都有痕迹,都已安放,转过身要多多拥抱这个世界。这是写作的意义、价值所在,往事没有随风,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故人,认识自己现在的生活和未来人生的走向。
这四辑我最喜欢前两辑,一辑写父亲,一辑写母亲,都和盘托出,毫无保留,真诚之外,能闻得见里下河人都熟悉的穰草气息,庞余亮是把故乡一直带在身上的作家,是会向生活索取素材的作家。开篇《四个“我”都在证明》,不足千字,将父亲母亲和作者的半生浓缩进去,那是一部可以写长篇的家庭内部纠葛,呈现锅底洼里下河村民普遍的命运。作者的童年是阴郁的,因为父亲的暴力,因为多子女家庭生活维艰,又因为锅底洼的地势,农人的生活在地平线之下。被洋辣子辣了,小孩子哪有不哭的。父亲看不得这副娘娘腔,拿起洋辣子在少年的胳膊上一按,用这方法暴力治皮痒,太疼了,呐喊和哭泣都逃窜到田野深处,只有六岁孩子张大的嘴巴。这是《丽绿刺蛾的翅膀》篇章中写到的一件匪夷所思的“亲子”故事,这疤痕无形。留在作者身上有形的褪不去的有七条。父亲去世,母亲见作者哭得伤心,反过来劝他:“你这么伤心干吗?他那么打你,你不记得了吗?”书里的父亲是不完整的,完整的父亲在天上。
散文创作不像小说需要虚构,也不像诗歌天马行空,得有个可抒发的实体,这是难的地方。正如作家张炜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所言:如果将作家的全部文字看作一篇篇通信或对话,大概在潜意识和意识中写给父母的最多。这本散文集中,我以为写父亲和写母亲的二辑,写到了普通人的内心深处。
庞余亮在诗歌、小说、散文、儿童文学等多个文类中穿行、切换,实现“文学转场”。“人生很漫长,实际上也很无聊,多写一些体裁进行文学转场,也是有趣的。庞余亮的文学起步从诗歌开始,但他说:“散文是最奢侈的写作。因为你要和盘托出自己。”读完这个集子,我发现写散文的庞余亮本质还是诗人。在《如此肥胖又如此漫长》中,夏天是怎么胖起来的?是伴随着鹅子换大毛悄悄胖起来的,是跟着南瓜套花结瓜慢慢胖起来的,是随着天漏大雨猛烈胖起来的。菜花地里的钻出的孩子像“金兔子”,楝树花落在水面像古时绣花鞋头面上的碎花,扬州有着水蛇一样的腰身,这样的句子,读得人眼睛发亮。作为地缘相近的阅读者,我有意无意的在阅读当中寻找熟悉的,也是久违的生活痕迹。菜刀砸蚕豆瓣,我看过,做过,也吃过。只是这样的蚕豆瓣烧的是大咸菜,而不是作者所说的小雨菜。记忆扒拉来去,确实没有雨菜印象。“所谓雨菜是指菜籽收获后,掉在地上的菜籽萌发的嫩油菜,母亲把落在田埂上和打谷场上的它们连根拔起,然后洗净腌好储藏起来。雨菜豆瓣汤中,那些黄玉般的蚕豆瓣在雨菜的包围中碎裂开来,像荡漾在碗中的一朵朵奇迹的花。这雨菜蚕豆瓣汤极咸鲜,极糯,极下饭。”我照录下这段,不是学嘴学舌拾人牙慧,我想在关于故乡日渐稀薄的印象中寻觅往昔,却隐隐绰绰,似梦似幻。故乡也成了我抵达不了的远方,唯有在这本书中重温。
母亲带给作者的生活费是用一根穰草捆着的烂角票,母亲的香草那个叫蘼芜串读成穿英的植物……母亲的恩施,子女无法偿还,唯有孝感,再无孝行。这本书献给文盲父母,也献给自己消逝的青春。
本书的后两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前面两辑,绕泥操场一圈这辑是乡下教书寂寞无助日子里看见的那些闪光的小露珠,都很简短,一百颗都不止。永记蔷薇花这辑是大学生活、散游足迹,那些相遇和成长。这些章节都带着浓浓的诗意,像春天的水面上,忽然钻出的一盘青嫩的菱角。